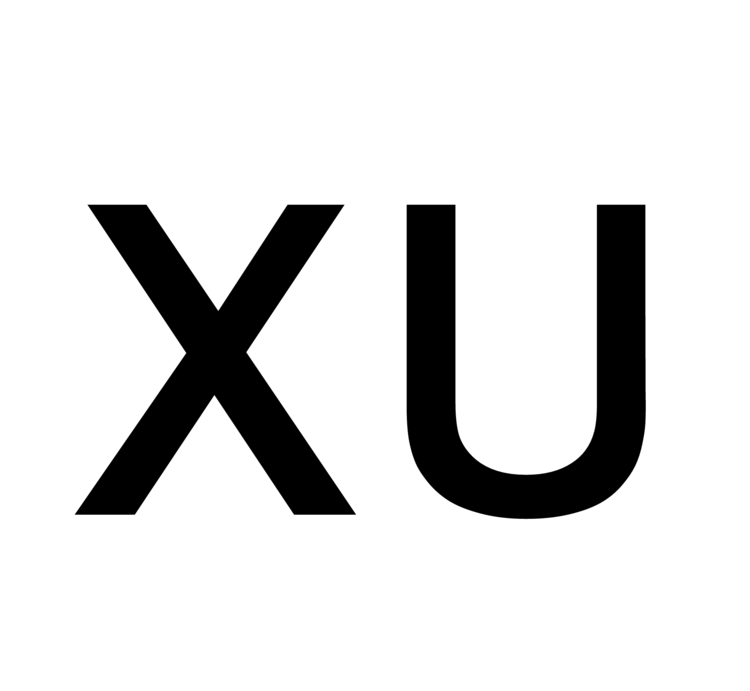相信你总有过这样的经历,心心念念想了很久的东西有一天终于得到了,于是就高兴得不得了。最近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发生在我身上,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特别美妙,所以我说给你听。
渥太华有一辆小火车,从城北开到城南,一共五站,我住最南边的一站。每天早上,我都要去车站搭个小火车去学校。通往站台的走道两边总会摆设满当天的免费报纸Metro,走道的尽头也总是站着一个穿绿色制服的发这报纸的老头。 我常常选择拿一份走道里现成的报纸,翻翻本地新闻,然后跟着人群挤上小火车。
有一次,我错过了小火车,错过了人群,只好坐在站台上等下一班。也是那天,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老头。空空荡荡的小小站台上,老头迅速地走了一遭,弯腰捡起了每一张被人遗弃的报纸,然后扔掉。
在这之前,我从不知道,捡报纸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我总以为他发发报纸就完事儿了。
在这之后,我开始观察,于是常常会看到捡报纸的这一幕。有几次看到他捡累了,就靠在站台的护栏边,喘着气,看着远方,一看就看很久。说实话,看着一位老人屡屡弯腰捡起这么多被人随意丢弃的报纸,有些心酸。
于是自那以后我开始默默坚持起一个很渺小的决定,就是每天接过他亲手递出的报纸,并且跟他说“Thank you”。我把这样的感激当作对他仅有的回报。
有这么三句话,老头每天重复无数遍:“Good morning”, “Thank you”,和“You are welcome”。他其实对每个接过报纸的人都这么说,可是当他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是特别高兴,好像我们就这么认识了,他也知道了有个人每天谢他一回。
而且我还私底下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Uncle Metro”。
有时和我的室友Wade一起搭乘小火车,我还会跟他叙述Uncle Metro的可爱之处,以及我每天蓄谋和Uncle Metro对话的计划,Wade听完总是笑着摇摇头。我也不管,自顾自兴高采烈继续执行着我的坚持。
日子这么一天天在赶小火车的早晨里开始,也在一天天搭夜班小火车回家的夜色里结束。
慢慢地,Uncle Metro成为了我自然而然的期待,有时看到他没来上班,还会替他担心,是不是病了还是怎样;看到大风天里他戴着手套,缩着脖子在站台上捡报纸,我还是会继续为他感到抱歉。但是我能做的还是只能说谢谢,并且珍惜我的那份报纸,不随手就这么扔了,增加他的工作负担。
也曾想过跟他搭个讪,问问他今天过得好么,觉得工作累么。想要了解他更多的愿望也一直一直在累积,可是从没有借口。
终于有一天,借口来了。教授布置了一个采访作业,要求我们做一个照片组成的视频,加上同期声,说一个故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Uncle Metro。
可是还是没有勇气,因为除了那三句话,我还真的从没见过他说过别的,我担心他是一个冷酷的人。
这个其实是我做记者最怕的事情。明明有个人我很想去了解他,明明有个故事我很想去说,但是有时候就是缺乏勇气。让我担心的不全是因为和陌生人说话,而是怕被陌生人拒绝,到时候断了的不仅仅是尴尬的对话,还有累积了很久的愿望。
我在家里挣扎了两天,挣扎得连短片开头的同期声我都想好了。先用 Uncle Metro的“Good morning. 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开场,重复个三遍,穿插点行人匆忙的脚步声,还有小火车进站的警铃声。至于照片,拍他捡报纸总是不能少的,还有发报纸呢,发报纸也不能少,我要看看他到底每天几点来车站。
总之,想法很多,就差勇气。一个人又在家自顾自激动了几天。
还好,勇气在作业要来不及交的前两天总算修成正果了。
我终于在一个星期三的早晨,挂着相机,牵着话筒,攥着录音笔,往站台一坐,不打算走了。我的战略是等站台人走光,等Uncle Metro报纸捡光,我就冲上前去。
这一刻到来的时候,我真的冲了。可你猜怎么着,他看到我走近他的时候,对我连连摆手,说“对不起,今天报纸发完了”。我说,我不是要报纸, 他继续说,“真的,今天报纸真的发完了。”我又说,“哎哟我真不是问你要报纸啊!”当时我的那个火热的心啊,凉了半截,想想算了算了,采访没戏了,这老头太轴了。
横竖横的一瞬间我跟他表白了,我说,“你听我说,我就是想跟你说谢谢。我谢谢你每天每天都站在老地方,我谢谢你每天给我一份报纸,我谢谢你让我每天早上来这个车站时都有些期盼。”
突然呐,老头的笑呐,我一看我就知道他的心融化了。
后来你也猜得到,老头答应了我一切的要求。
跟踪了他两天,从早上五点半到九点,拍了将近500张好照片,40段好录音,故事的结局是做出了一个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