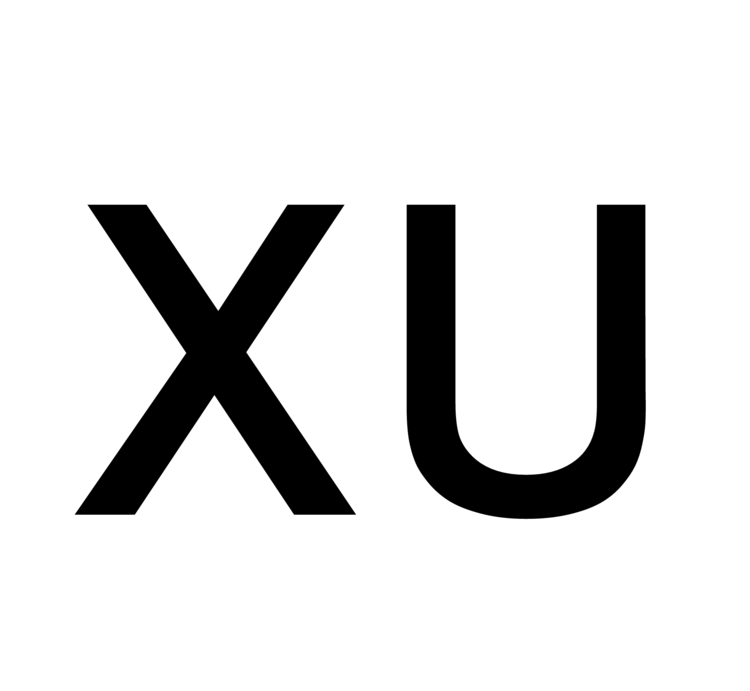“你去非洲工作么?”我问。
“对,我去刚果金。你呢?”她问。
“卢旺达。”我说。
这段对话发生在机舱左前方的厕所门口,跟我说话的是个三十出头的中国女人。我的目的地虽然是东非的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却是我要到往转机的第一站。在这架飞机上,也能一窥从国内去非洲的都是哪些人。
黑人不多,四五个;白人也少,只见一双。虽是观看动物大迁徙的旺季,穿着体面的旅客并没有想像的多,大约十几个。像我和我说话的这位这样年纪相仿、性别相同的中国女人,也非常罕见。绝大多数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国男性,皮肤黝黑,操着一脸的疲惫。
推搡地下了机场地面大巴,揪着大袋小袋登上短短二十层拥挤的台阶,他算是很早就进了机舱的一位。放完行李,他就迫不及待地拆开座位上为乘客准备的物品,戴上了里面柠檬黄色窄窄的口罩一只,之后开始伸长脖子翘首张望陆续进舱的形形色色的人。
我穿过走廊,第31排,坐下。瞅了瞅,没毯子,只有一只很小的密封塑料袋,里面一把牙刷,一支迷你的牙膏,一块姜黄色的小毛巾,还有一只窄窄的柠檬黄色的——但不是口罩,是眼罩一只。半信半疑地又看了那男子一眼,看到的却是他自信满满、一副登机经验十足的面容。算了。
随着大多数人坐定,许多男人开始很有经验地脱下皮鞋、牛筋鞋、球鞋,套上了塑料袋里的那块姜黄色的——但不是毛巾,原来是袜子一双。尴尬了。
飞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我和大部分人一样,开始瞌睡。才闭眼,我就闻到从前慢车上特别熟悉的味道,心里一惊,安慰自己这不会是真的。又微微地、小心翼翼地,但是深深地吸气体味了一番,我瞬间就心都凉了。没错,是脚臭,最传统最顽固的那种。
不敢面对现实的我勉强睁开双眼,怯怯地四下寻望,才瞟到左后方,一只海军蓝色旧皱的袜子连着得那二郎腿恨不得都搭在我肩膀上了。我本想用道义的、甚至是夹杂乞求的眼神去瞪这个左后方的男人,可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回敬的审视我的眼神一点也不马虎。
算了,抓了一撮还没汗臭的长头发摆在鼻子底下,扭过头闻着右边即将去往肯尼亚坐热气球的父子俩身上残留的清新的洗衣粉味,我努力入睡。
没睡多久,身边有人靠近,我闻到这个人张开了他臂膀的“狐”线,从上方行李箱取下了什么东西,接着弯下身,开始翻他的行李。幸亏这人到往,左后方的袜子终于因为空间有限放下了。只是我还没缓过气消受短暂的气味空白,一股浓浓的咸鱼味随着身边这个人行李包的打开,瞬间充斥了方圆一米。
好奇心让我又睁开眼低头看。我看到包里有一袋火红的花生米,两盒老坛酸菜面,还有一些里三层外三层裹着的疑似家乡菜。我心头一阵温暖的酸,想想到往再远的打工仔,都不会忘记捎上属于远方家乡的味道。
让我心酸到要哭的味道,发生在他放回行李离开后。
那是又一波更加浓烈、集中、甚至尖锐的——脚臭。半米以外,我看到一对崭新的、黝黑而粗糙、裸露而大方的双脚,努力搓动着试图要挂靠在前方座位后背的杂物袋上。最后当然成功了,而且这样的姿势保持了很久,很久,很久。
我解开安全带,起身,打开朝着我吹的冷气旋钮,满怀希望这是个很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坐下的一瞬间甚至有些为自己急中生智而洋洋得意,扭过头,想睡。经过五分钟的等待,才发现自己真是在做白日梦。
在焦虑的情绪中已经无处可逃的我,最后还是决定放弃睡眠,起身到处走走,走到机舱最前方,停在拥挤了三四人的厕所门口,于是便有了故事一开始的那段对话。
只是没想到,最终轮到我如厕时,那一开门,又有一种薰天的新品种气味迫不及待地拥抱了我。马桶盖上、地上、甚至墙上,都有着气味的活泼的载体。
我憋着气故作镇定地逃离。返途中,放眼望去,多少民工七倒八歪地横竖在座位上。他们屁股底下埃航飞机里那些深绿色的座位,突然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新近才停开了的、却运输过数以亿计的打工群体的绿皮火车。
虽然时代更新了,载体高级了,目的地更远了,但汤包里的馅儿始终还是没变,皮一开,丰富的种种一涌而出,都是喜匆匆地冲着糊口,奔着建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