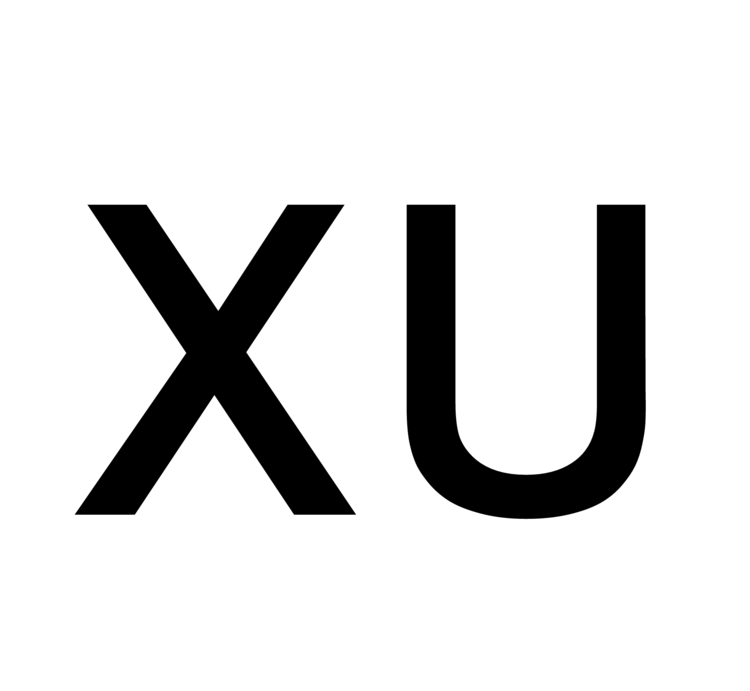期末已至。考试和论文急坏不少学生,但也有一件事情吓得坏老师,这件事叫做Evaluation(教学评估)。
Evaluation的程序很有意思。到了最后一节课,教授揣一个大信封进教室,课末,每个学生都会拿到一份信封里的表格,接着教授默默地走出教室,在门外探头探脑,等学生填完了以后,才走进来,收集完,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舔一口信封上的干胶,非常诚实地将信封再密封起来。
表格的绝大部分被各种事无巨细的打分题目占领,最好的例子有一题问你这个老师迟到不迟到,0到5分你打个勾吧。
我最喜欢的是表格的最后一个题目,问你,还有什么你想跟这个老师说的,你写下来,等你拿到期末成绩以后,你的老师会看得到这句话。因为是匿名的,所以你写什么都可以。
Dr. Kelly是我的摄影课老师,我在他的Evaluation表格下方写下这么一句话:
“I wish you were my grandfather.”
我知道这样的Evaluation,即使是在加拿大,也不是一个传统的Evaluation,可是写下这样的评价,是出于我的内心:因为我多么希望,在我一路长大的途中,可以早些遇见他,有他不断地引导我的人生观,让我成为一个更加善良和正义的人。
他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说过一个故事。
四十年前的一天,那是他第一天做新闻摄影记者,报纸所在的城市里发生了车祸,他被编辑派去现场拍照。他说,他拍到了汽车的残骸,可是他迟疑了很久,最终没有走上前去拍摄司机尸体的特写。回到报社后被编辑指责,他便主动辞去了工作,因为他有自己不想也不能打破的底线。
对于拍不拍照,拍怎样的照,每个人,每间新闻室都有不同的答案,因为没有人对道德和专业之间平衡的界限持完全相同的观点,所以争论到最后总也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
Dr. Kelly有他的答案,他说也许摄影记者可以不假思索地在各类现场对各种细节进行捕捉,再等回到新闻间待编辑慢慢挑选,将道德的担子转嫁给编辑。可是,真正的道德是在摄影师按下快门前的短暂瞬间产生,是那一瞬间的本性决定成品,而不是在于之后的挑选。
我八年前在文正的课堂里,学到编辑是媒体的把关人,现今又学到一课,原来记者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把关人。
除了道德的引导,Dr. Kelly也让所有的学生成为更自信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最好的照相机,是你正在用的那一部。”无论是手机,傻瓜机,还是单反机,摄影不在于机器,而在于你的内心。
他最欣赏我的一份作业,是我拍摄的校园的秋天。镜头里是俯瞰的排水沟,沟上挂满各色的落叶,沟边是一只鲜红的落在地上的野苹果。我说,秋天不一定是体面的金黄的落叶,那些不巧落在水沟上的种种,也是生命。
Dr. Kelly说,那张照片说服了他我可以成为很好的摄影师。而唯独那张照片,是我所有作业里仅有的用手机拍摄的一张。
所以Dr. Kelly有时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可以解答我迟疑很久的迷思,无论是对于新闻道德,还是对于器材的追求。我曾在一封写给他的邮件里告诉他,“我对摄影的热情,曾因为种种原因被埋在一层薄薄的落叶下。而今是你,轻轻地走过来,温柔地将落叶片片扫去。”
在最后一节课结束的时候,我留在最后一个才走,跟他告别的时候,眼泪就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这次在加拿大的书念完,就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从大学毕业了,我也应该再也不会在课堂里遇见Dr. Kelly了。
安慰人心的是,他一路把我送进了电梯,电梯关门的时候,他竟然挥挥手,对我说,
“Goodbye, my granddaugh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