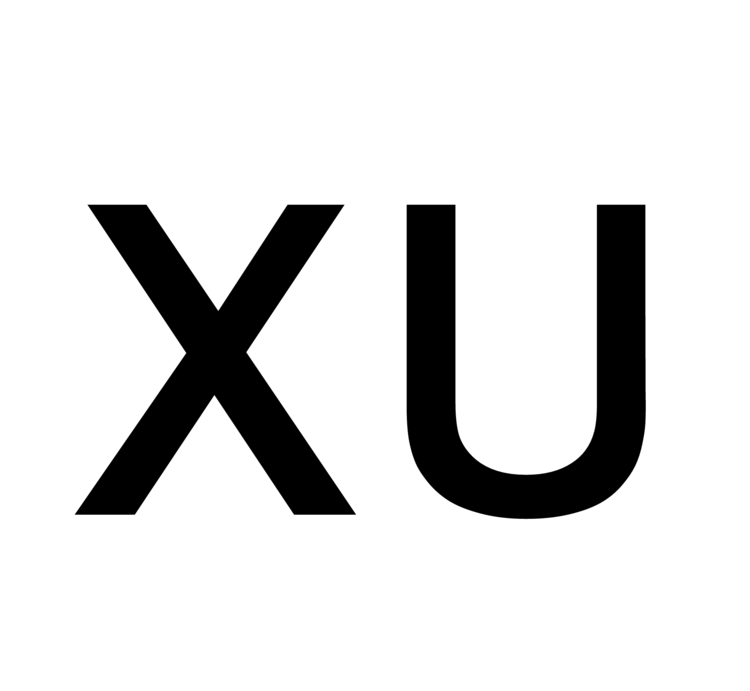“Wade我做了点红烧肉,你要吃点儿么?”我问。
“呃,我现在不是很饿,所以我想还是算了。但是还是谢谢你问我。”Wade回答。
大胡子Wade是我的加拿大室友,这个对白常常发生在我烧了很多中国菜之后。他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得看他当天饥饿状况和心情。但他总是对我的邀请表示感谢(Appreciation)。
试想一下如果Wade只在每次吃了以后才对我感激,而每次不吃的时候都只冷冷地说一句“我不饿,我不吃。”那么说实话,我很难想像我对邀请他吃红烧肉的热情会一如既往的激昂。
因为我需要被感激。而且被感激的不应该仅仅是热气腾腾的红烧肉和我烹制过程中的辛苦等待,也应该是我乐于付出和分享的心。
我不仅希望我的付出被人看到,也希望它不被人视作当然。如果在被认同后还能得到对方的口头的感激,这就像是一个付出与回报的回合被完完整整地实践了。
Wade和我的对白,以及很多当地人与我类似的对白,渐渐教会了我如何使用简单的一句“谢谢你”,也教会我反思很多我之前遇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人际关系。
首先是我与家人。我的父亲是家里的主厨,我和他之间关于食物的对白大致有以下几种。最好的一种是我说:“啊呀爸爸这个糖醋鱼真好吃!”接着我的爸爸欣慰地笑着叫我多吃点,然后我埋头猛吃;常出现的一种是我和母亲埋怨:“喔唷今天的这个红烧鱼咸了!”我的爸爸有时会为自己不符合逻辑地辩护一两句,比如说这次的酱油比较咸,但大多数时候他也只好认了;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我没胃口吃饭,在父亲再三催促下,我吼一句:“哎呀你烦死了,我说了我不饿。
我猜想我的这些对白应该不是个例。可是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多么糟糕的表达,因为没有一顿饭我真正地表达了对我父亲劳动的感激,也从来没有一天我真心表达了对我父亲关怀的感恩,即使是偶尔地对食物表示出的肯定。他的苦心直到我开始为他人烧菜时才深有体会:从计划时的满心欢喜,购买食材时的挑挑拣拣,烹饪时的反复品尝,到最后的小心装盘,每一分钟都承载着值得被感激的爱。可惜我没这么对爸爸说过。
其次是我与老师。至今都令我无法介怀的一件小事发生在小学里。当时班上有个女孩子写作文很好,语文老师就想拿她的作品去市里参赛。能看得出老师很拿这件事当真,因为她偷偷地找我要我在田字本上一字不差地为那个女孩誊写一遍那篇作文,据老师说我的硬笔书法可以让女同学有更大把握给学校争光。誊写的时候我自作聪明改动了一个字,我自以为那样读起来更通顺,不料被语文老师痛斥一顿,原因无需多讲,结局也无疑是我必须怀着胆怯、不满、以及渴望补救的复杂的心情重新抄写一遍,直到老师点头肯定。
十年之后回母校探望,见到当年的语文老师。课间进来一个黄毛小丫头,左手臂佩戴着两条鲜红的杠,跟当年的我一样。她聪明地紧挨着老师,在骄傲地汇报过自己完成老师分配的任务后,几近阿谀地讨要更多的任务。她走前老师只干脆地说了一句“好了去吧。”她便蹦蹦跳跳地出门,你都能看出她满身的自豪,和那么一种微妙的,像时拥有与老师之间某种神秘契约的安全感。她走后我对老师说现在的小孩真懂事。老师没有嗅出我的无奈,反倒很替小朋友的明事理倍感骄傲。现在想来,老师怎么着都欠很多小孩很多句“谢谢你。”
师生之间的这种回合也能衍生到任何上下级的关系,也许学生为老师做事是为学业,部下为上司做事是为工作,但是这类关系不等于不能够感恩,因为再复杂的关系,简化到最后也是人与人。
每个人都值得被平等对待,每个灵魂都值得被感激。希望我和你都能记得多说。